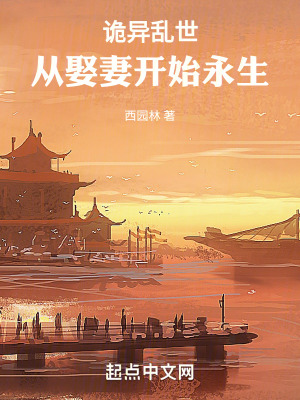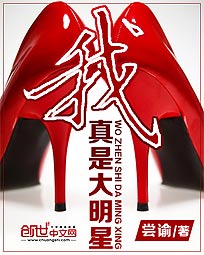半生烟云 二十七 长临工 下
readx; 师徒关系的改善缘于一场病。农工宿舍流行泻肚子,颉颠尤其严重,拉脓拉血水米不进。叶小娜随舅舅牛秋石来良种站出诊。
三个月不见,小娜脸色红润长高不少,穿白大褂脖子上挂听诊器。牛大夫确诊是急性菌痢,每人派发口服药。蒋乐生说颉颠的病情严重,央求小娜给他静脉滴注,老头很快转危为安。
深秋的一个雨天傍晚临下班,颉颠突然问他看过三国没有?乐生回答初二暑假里看过。颉颠问可记得官渡大战?他说当然记得,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嘛。颉颠又问:曹操手下有个叫王垕的会计,记得吗?
蒋乐生狐疑不解:没有呀,那年代哪有会计?
古时后钱粮官就是会计。颉颠以略带伤感的口气叙述:曹操久攻袁绍不下,面临军粮断供危险,密命钱粮官王垕大斗改小斗,一天粮食匀做三天吃。王垕明知道克扣粮饷是死罪,但主公命令不容违抗,只得遵命照办。
蒋乐生说:这钱粮官后来好像被曹操杀了。
老头点点头,沉浸在自己的叙述里:大斗改小斗兵士怨声载道。一旦发生哗变不攻自溃。曹操对王垕说吾借汝人头一用,汝妻儿老小自有吾照应。手起刀落将其枭首,人头挂旗杆顶示众。后续军粮运到,曹操重新发起攻势,将士奋勇冲锋大获全胜。你说说,王垕死的冤也不冤?
浑浊的泪水在老头眼圈里打转,蒋乐生吃惊地问:师傅你怎么啦?
于是颉颠向他袒露自己的身世:哪年哪所大学毕的业,哪年哪月进船厂,做事用心被聘为总会计师,厂长令他做假帐偷税——当时全国偷税成风,要不怎有后来三反五反?厂长说你会计水平高,做的帐出不了事,出事我负责。不了出事后他推得一干二净!这白脸曹操让我充当了一次王垕的角色!
颉颠泣不成声,胡茬上闪着泪光。来北大荒前最后一次会见,老婆哭成了泪人,捧出离婚协议对他说,为了儿子你就签了吧!
蒋乐生见他哭得伤心,安慰道:师傅别难过,一切都过去了。
颉颠的话象开闸的渠水:后来才知道,我离家不久老父也死了,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宗不少!唉,我的归宿,也就是棋盘山半岛花园了。
老头沉默片刻止住泪慨叹:创办立信会计学校的潘序伦,号称中国近代会计之父,是我的大学同窗,责怪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,不懂得当会计危险系数高!
蒋乐生截住话问:师傅,危险系数高什么意思?
老头说,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,可见钱财二字的份量。要守住钱袋绝非易事!你记住,说一千道一万,犯法的事坚决不干!
颉颠借给他一本潘序伦主编的《会计学》,其中有两章是自己的得意之作。
没有业务实践读《会计学》味同嚼蜡。学问学问一学二问,在颉颠这里行不通。向他请教只答一两个字“对”“不对”“可以”,或者“自己动脑筋”。老头说问人只学到皮毛,自己“悟”才明白精髓——也许他以此作为不肯施教的借口?
颉颠对乐生的业务进步喜忧参半。元旦前会计检查,任科长当他面夸他名师出高徒。老头听了虽高兴,想到徒弟学成他将被弃之不用,心中不免凄惶。
应了潘序伦大师的话,会计这行危险系数确实高。
这年的春节物资依然匮缺,猪肉少得可怜:干部基本工人及其家属每人一斤,就业农工半斤,犯人只有三两。
王化举给生技科打报告,请求淘汰两头老牛,承诺上交场部机关部分牛肉。
“秃角”“老黑”的大限到了。刽子手便是会拉手风琴的王长脖。判刑前他是大连食品厂屠宰工。血腥的职业和风雅的业余爱好集于一身,令人匪夷所思。
两头牛皆为雌性。“秃角”幼时淘气,与伙伴角斗折了一只角;“老黑”温驯,名字由“大黑”而“老黑”。它们犁地拉车多年育有满堂儿孙,如今毛色暗淡老态龙钟,站着打瞌睡躺倒了懒得起。王长脖将它俩牵出牛圈,拴在相距不远的两棵树上。它们不知死到临头,耷拉着眼皮呆呆伫立,任凭孩子们奔走呼叫一动不动。两头小牛犊撒欢儿跳前跳后,不知是谁的后裔?
王长脖摘下狗皮帽甩掉大衣,往手心呸呸吐两口唾沫,拎起十二磅大锤,对准“秃角”脑门便是一锤。“秃角”像堵墙轰然倒下
二十七 长临工 下
-
新文案: 大病之后,眠棠两眼一抹黑,全忘了出嫁后的事情。幸好夫君崔九貌如谪仙,性情温良,对于病中的她不离不弃,散尽家产替她医病……眠棠每天在俊帅的夫君的怀里醒来,总是感慨:她何德何能,竟有此
-
暫時無小說簡介
-
暫時無小說簡介
-
暫時無小說簡介
-
意外穿越成最后一代人皇,不甘心自己成为圣人的玩偶,让亿万万人族成为天庭诸神的傀儡…… 重生的帝辛踏,毅然决然的踏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封神之路! 怼女娲、叱太上、收龙族、定洪荒
-
简介: 穿越四合院世界,他只想安安静静的生活,种种田,钓钓鱼,悠闲市井之间,苟且人性边缘。 做个俗人……
-
一心想当明星的张烨穿越到了一个类似地球的新世界。电视台。主持人招聘现场。一个声音高声朗诵:“在苍茫的大海上,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,海燕像黑色的闪电,在高傲地飞翔……暴风雨,暴风雨就
-
演员?演员的尽头是带货!我可是大网红,做演员?脑子进水了?
-
暫時無小說簡介
-
“你数理化不及格,大学都难考。看看隔壁小陆,那孩子打小就聪明,他数理化也差,依旧上了北大,说是参加了什么北培杯保送的,你怎么不去试试?”“妈,人家顾陆是知名作家,《平面国》《解忧杂货铺》《人间